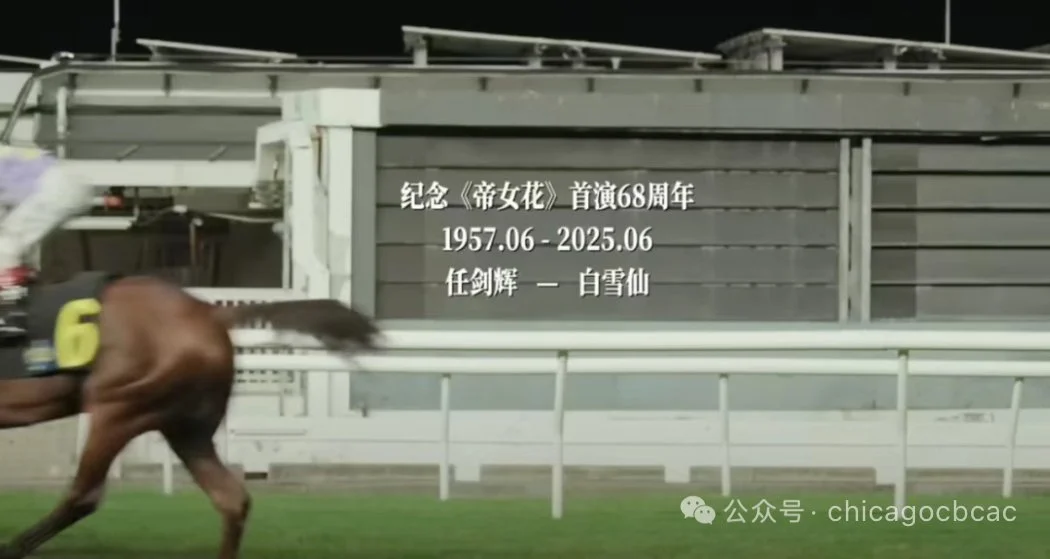人物|在芝加哥,跟21歲的粵曲傳承人聊聊他心中的“大展鴻圖”
原創 天舒 華埠Spotlight
2025年8月1日 18:05
圖片來源:《大展鴻圖》MV
“別墅裏面唱K,水池裏面銀龍魚……”這個夏天你有沒有被攬佬這首《大展鴻圖》洗腦?
除了粵式“無厘頭”的鬼畜歌詞,極具魔性的伴奏旋律讓這首說唱提供了豐富的二創空間。那句不斷循環的粵語唱詞——“霧煙暗遮世外天,有仙山化作月台殿”——采樣自經典粵曲《帝女花》。
創作團隊在MV開頭寫道:“紀念《帝女花》首演68周年。”對于不少內地的居民來說,這可能是他們人生中第一次聽粵曲。而廣東居民們也發出感歎:“沒想到連我小時候聽的《帝女花》也能翻紅!”
《帝女花》講述的是一段淒慘的殉情故事。幾十年後,它搖身一變,成了年輕人一邊喝酒一邊跟著晃的音樂。有些人調侃這是“禮崩樂壞”,但對于當下的粵曲乃至粵語文化來說,關鍵不在于爭論“如何傳承”,而是要先保證它“可以傳下來”。畢竟香港電影和TVB的黃金時代一去不返,15年前在廣州的撐粵語行動越來越像一個時代的悲情注腳。
奇妙的是,在本土顯得式微的粵語文化,卻隨著廣東移民的遷徙,在大洋彼岸的美洲土地上落地生根。盡管越來越多人也開始使用普通話,但在芝加哥唐人街,粵語仍然是“官方語言”。而以粵語為載體的粵曲、嶺南舞獅等藝術形式,依舊活躍在社區裏的各式聯歡會、節日遊行中。
在這些粵曲、舞獅乃至功夫表演中,有一位21歲年輕人的身影。他叫黎家銘,5年前隨父母移民美國。在這位被被唐人街前輩們寄予厚望的“後生仔”身上,人們或許能看到粵語文化的生命力和美。
黎家銘今年21歲,每周四他和同伴在譚繼平公園吊嗓子,練習粵曲
圖片來源:樹溪/Chinatown Spotlight
一起玩音樂
每周四的早上,從芝加哥市中心乘坐水上巴士(Water Taxi)到唐人街譚繼平公園碼頭,你會看到一個留著短寸、體型微胖的年輕男生和一群大叔大爺在排練曲目。
這個年輕人就是家銘。他早早背上黑色小挎包,推著裝滿音響設備的手推車,到譚繼平公園裏吊嗓子,熟悉樂器,沈浸在粵曲的故事裏。
一年前,家銘經熟人介紹加入芝加哥廣州協會曲藝社。看著年紀輕輕的他,曲藝社的叔叔阿姨不禁懷疑:“你會不會玩啊?”家銘自信地回答:“你隨便拿給我一個曲子,我都能彈給你聽!”
由于奶奶愛好粵曲,家銘自小就耳濡目染。當時的他不太能理解歌詞,卻被悠揚的旋律深深吸引,于是自己摸索著學起裏頭的樂器。阮,胡琴,鼓,笛子,唢呐,家銘樣樣都會,“唢呐的吹嘴選用蘆葦做的最好”, “演粵曲要跟著鼓點走位”,“牛骨頭打磨秦琴撥片要……”談到這個話題,家銘總是滔滔不絕。
除周四外,每周二下午是另一個固定排練的時間。只要沒別的安排,家銘都會來到曲藝社何團長位于華夏新村的家裏,和十幾位社員們一塊兒擠滿整個客廳,開始長達四小時的粵曲排練。客廳裏擺放的白色櫃子,是一個小小的粵曲檔案室,裏頭放著一個個用紅色馬克筆標注曲牌名的塑料袋,塑料袋裏裝著一摞摞散發著艾草味的手寫曲譜。
家銘從京都念慈庵的盒子裏,拿出自己的吹嘴和松香,開始調試樂器,也幫身邊的叔叔調音。十二點一到,一對叔叔阿姨站在玄關處對唱《同是天涯淪落人》,底下的人翻開曲譜,無需磨合,直接就開始了流暢的伴奏。外人很難明白他們如何達成這種默契,家銘解釋說要懂得聽裏面的領頭樂器,跟著它的節奏和韻律走。
家銘說:“粵曲唱的是人間的喜樂悲哀,表演粵曲的人是要有靈性的,要能走進角色內心。”
粵曲的曆史,最早可追溯到清道光年間的“八音班”,民國以後由當地的女伶發揚光大。作為一種民間曲藝形式,粵曲分三種唱腔,以廣東方言演繹,融合越劇和其他嶺南地區音樂特色,故事大多取材自民間傳說和古典文學,一直流傳至今。
在他看來,情感是粵曲表達中最重要的部分,空有唱功和技巧,是無法演繹出精髓的。他示範如何壓低自己的聲音,如何在樂句結尾時更婉轉,在文武生的角色裏切換,用不同的走位方式體現人物的氣場。
家銘和社員們一起在曲藝社團長家中排練粵曲
圖片來源:天舒/Chinatown Spotlight
家銘在譚繼平公園河邊練習二胡
圖片來源:天舒/Chinatown Spotlight
在譚繼平公園,家銘的練習會伴隨一些小插曲。幾位來公園練武的叔叔路過,他從小推車裏給他們一人掏出一瓶礦泉水喝。叔叔們想借用他的音響唱些流行音樂,家銘也耐心地為他們調試音量,幫他們點歌切歌。
家銘完全不覺得自己的練習被打擾,反而還很高興。“我一個人在家練習是很悶的,在外面大家人多,可以都一塊兒來玩,人越多越好玩。”
從水上出租車上下來的乘客們,紛紛掏出手機對准他們錄像。畫面裏,叔叔們對著麥克風唱著Beyond,家銘靠河的長椅上拉二胡,來自兩代人的旋律,和諧地交融在了一起。
雄獅少年
在16歲隨家人移民芝加哥之前,家銘在廣東省江門市蓮塘村生活。三歲那年,父親領著他,摸了摸舞獅頭的胡須,年幼的他自此便“感受到一種召喚”。只要他聽到舞獅表演的鑼鼓聲,就會被定在原地不舍得離開。
9歲那年,家銘正式成為一名舞獅學徒。師父教給他的第一課,不是舞獅的基本功,而是做人的基本功:“要尊師重道,孝敬父母,忠厚誠信。” 這句教誨深深影響了家銘,不僅被他時常提起,也成為了他約束自己品行的守則。
為了能舉起重達35斤的獅頭,年幼的家銘要用啞鈴做力量訓練,從輕的獅頭開始練習,逐漸加重量。對他而言最大的挑戰是恐高,因為害怕踩高跷一類的動作,他曾經想過放棄舞獅,暫停了訓練。而兩周後,沒有被誰勸說或逼迫,他就主動回到了師父家裏,開始了克服恐高的“脫敏療法”:站在一個立起來的長凳上往下看,直到自己不再感到害怕為止。
談起這些訓練的辛苦,他總是雲淡風輕的。過年期間還要連著兩周和師父一塊兒去附近鄉鎮表演,在他看來是“不花錢就能四處走走”的難得體驗;因為支撐粗糙的木棍而長起來的水泡,在他眼裏也算不了什麽。他化解一切問題的秘訣,是一句“沒辦法啦”,帶著廣東口音的俏皮音調。“因為是自己愛好的東西,所以就是得面對。只要熱愛,就沒有問題。”
在譚繼平公園,家銘正在練功
圖片來源:天舒/Chinatown Spotlight
或許是長年累月刻苦訓練的結果,來到美國後的家銘也一樣自律,沒有半途而廢。他不好意思地說美國的食物營養太好,自己長胖了一些,但因為他每天從紮馬步這種最基礎的功夫練起,自己身體的靈活度一點也沒退步。他不吃生冷,油膩和辛辣的食物,保證身體狀態。他很驕傲地說:“我好多朋友玩遊戲都花很多錢,但我不玩遊戲,怕沈迷進去,也從來沒有給遊戲充過錢。”
初中時,家銘身邊的同學們都打起了《王者榮耀》。同學們對舞獅的評價是,“沒有遊戲刺激”。
故事新編
多年來,家銘常常覺得“知音難覓”。移民之後,他與當年的師兄弟們也斷了聯系。芝加哥熱愛曲藝的年輕人屈指可數,家銘的社交圈也大多是些長輩。他不是沒想過帶著自己的同輩朋友了解曲藝文化,可他們“一聽到敲鑼打鼓就跑了”,甚至有朋友會聯想到“破地獄”(為逝者超度)的儀式,覺得犯了忌諱。
家銘計劃,等自己的弟弟再大一點,就教他舞獅。可他也不指望弟弟能成為接棒的下一代:“小孩長大之後會接觸很多新鮮的愛好,我也不知道他會對舞獅感興趣多久。”
盡管近些年,國內出現了類似《大展鴻圖》和《雄獅少年》這樣的從粵語圈文化走出來的現象級作品,但它們也沒能掀起一股學習民俗曲藝的浪潮。舞獅表演經濟收入低,職業化發展受限。由于語言限制,故事傳統,粵曲很難像抖音神曲一樣爆紅,導致從業者們青黃不接。
在家銘的老家蓮塘村,如今只剩下3位還在舞獅的年輕人。家銘的師傅也年過古稀,沒體力再像年輕時一樣遊走四方招攬徒弟。上次回老家,家銘發現不少年輕的小孩都成了“本地撈”,講話時只能粵語與普通話摻雜著說,甚至只說普通話,與只聽得懂廣東話的老人就更沒辦法交流。
在推廣普通話的政策下,不少廣東的年輕人不會講粵語,許多道地的粵語俚語也被普通話的表達所替代。家銘認為保護好粵語是當務之急,因為這是廣東人的文化根源所在。他回憶,自己所學的粵曲知識,樂器的保養與挑選方法,大部分都是從老一輩的口中傳下來的,是書本上學不到的。一旦語言和文化産生隔閡,代際間的傳承,自然會變得更困難。
“老一輩人的問題是‘死守一盆水’,這樣一來水就不活了,得學會慢慢融入現在的社會”,家銘說。“無論是舞獅,還是粵曲,不創新的話是很難傳下去的。像我們現在有時候也可以跟著流行音樂舞獅,但保留傳統還是很重要的。”
家銘提到在廣東順德,有一群年輕人開始推廣“新粵曲”,融入西方的樂器和編曲元素,重新演繹老故事。談到《大展鴻圖》對《帝女花》的改編,家銘也不排斥:“起碼他讓一個本來很悲傷的東西,變成了一個更多人能聽下去的,開心的東西。”
為了給傳承文化盡一份力,家銘現在手底下也有兩個徒弟,一個10歲,另一個上高中。家銘用當年師父訓練自己的方式訓練徒弟們,讓他們紮紮實實地學好中國武術的基本功,不要急著融合其他國家的武術。但他也做出了“變通”:“我不讓學生們叫我老師,不想和他們有距離感。而且有些美國長大的小孩,他們也不知道‘師父’是什麽,所以我們就做朋友,互相學習交流。”
他曾教過的一位學生,如今去了紐約。學生跟他說,自己在紐約也要把耍關刀和舞獅的技術繼續發揚下去,這成了緩解家銘孤獨感的最大的安慰。
家銘的偶像是葉問,他能一字不差地背出他的名言:“處世樹為模,本固任從枝葉動;立身錢作樣,內方還要外邊圓。”
但他從不奢望成為葉問這樣的“一代宗師”。他總把“一山更比一山高”挂在嘴邊,謙虛地稱自己是個“業余愛好者”。盡管他也想開一家結合曲藝和舞獅的場館,向偶像看齊,但他明白,以舞獅或者曲藝謀生會帶來不少現實的挑戰。“我得考慮做這個能不能養活我的家庭,維持生計。所以我希望我能先賺夠一筆本錢,或者有人願意投資和我合夥,再考慮開武館。”
以前讀書的時候,同學們說他嗓門大,給他起了個筆名叫“龍鳴”。“龍”要用繁體字的,看上去更有氣勢。如果有朝一日這家武館能開起來,他會用自己的“龍鳴”命名它。
參考資料:
深度 | 普通話普及之下的粵語:被漸漸丟失的“身份證”